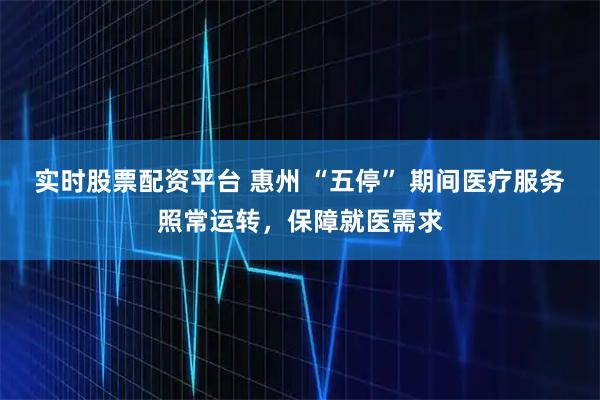运河渡口旁的清溪镇,终日里人声鼎沸。水陆码头往来不息,活像口刚烧开的沸水锅,烟火气裹着腥气漫全镇。
镇西头的柳守义,开了间露天茶摊。竹棚底下,天天坐满扛活的苦汉子,茶碗沾着厚油,桌案黏手得很,生意倒也还算兴隆。
变故起在街对面,忽然开了家茶舍,名唤“净心斋”。掌柜姓苏名珩,三十上下年纪,生得白净,常着件洗软的青布长衫。
这苏珩,在镇里人眼里就是个怪人。茶舍地面扫得能映出人影,桌椅腿必擦三遍才罢。客人洒半滴茶水,他立马拿白绢擦得无痕。
糙老爷们儿进店都犯怵,生怕碰脏了地界儿。柳守义的媳妇撇着嘴念叨,纯属装腔作势,这般经营,撑不过三月就得关门。
展开剩余78%可奇了怪了,净心斋日日冷清,苏珩却从不见愁容。夜里常有人见他在窗边小酌,小菜精致,青瓷酒壶慢品,倒像个避世的富家子弟。
柳守义心里也犯嘀咕,自家茶摊虽脏,却能实打实挣钱。那苏珩守着冰窖似的茶舍,难不成靠喝西北风过活?
那年秋末,京里派来周御史巡查河道。官船刚靠岸,御史便皱了眉,码头腥臭味混着汗味,实在呛人难挨。
师爷四处打听清净去处,终是寻到了净心斋。御史一进门,见窗明几净,案头青瓷瓶插着野菊,心头烦躁顿时消了大半。
苏珩不卑不亢地奉上茶水,茶汤清亮,能照见杯底茶叶。周御史呷了两口,连连称好,当晚便留在此处吃了素斋。
两人就着一碟茴香豆、半盘凉拌木耳,彻夜长谈。临走时,御史拍着苏珩的肩赞叹,乱世之中能守这份清净,实属难得。
这话很快传遍清溪镇,谁都知道,净心斋的苏掌柜,得了御史大人的赏识。柳守义听了,心里酸溜溜的不是滋味。
他望着自家茶摊的瓜子壳、痰迹,又瞥见媳妇用油腻抹布擦桌子,脸上一阵发烫。这是他头一回觉得,自家地界是真脏。
打那以后,净心斋常来些穿长衫、摇折扇的体面人,都说来沾沾这儿的清气。苏珩依旧如故,擦杯子比往日更细致。
柳守义的茶摊依旧人来人往,可他见了满地狼藉就心烦。一回有客人咳痰在地上,他竟忍不住吼了起来,把客人气走了。
媳妇骂他发神经,自家茶摊养活全家十年,苏珩是天上人,犯不着跟着攀比。这话戳中柳守义的痛处,他竟疑心苏珩是装干净。
没过几日,镇上货郎嚼舌根,说三年前邻县有个苏账房,极爱干净,后来卷了东家银两跑路了。柳守义心里咯噔一下。
他越想越觉得苏珩就是那苏账房,天天擦桌子是怕留指纹,不与人深交是怕露马脚。一个歹念,在他心里慢慢生了根。
他买通净心斋隔壁的小伙计,得知苏珩每晚关店后,用特制皂角水擦茶具,还会提水桶去后院老槐树下倒水。
柳守义动了坏心思,从药铺买了无色无味的痒粉,又找了块油污破布,趁夜混进苏珩晾在院里的白布中。
他又摸黑到老槐树下,挖了个坑,把包好的烂鱼肠埋了进去,就等看苏珩出丑。
次日一早,天阴沉沉下起小雨。苏珩收衣服时没细看,拿那块脏布擦桌子,没多久就浑身发痒,起了大片红疙瘩。
更糟的是,烂鱼肠被雨水泡发,臭味顺着风飘进茶舍。偏巧周御史这天又来巡查,一进门就皱紧了眉头。
御史见苏珩脸上红一块白一块,衣衫沾着污渍,与先前清爽模样判若两人。柳守义赶紧凑上前,假意提醒有蹊跷。
周御史本就爱干净,见此情景,冷哼一声,骂了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,甩袖便走。这话彻底毁了苏珩的名声。
净心斋关了三天门,镇上流言四起,人人都骂苏珩是伪君子,表面干净内里龌龊。
第四夜,柳守义喝了点酒,路过净心斋,见苏珩蹲在老槐树下,拿瓢一勺勺往树根浇水,月光下的背影格外单薄。
柳守义故意上前找茬,劝他别太讲究,水至清则无鱼,自家茶摊脏却红火。
苏珩缓缓转身,月光下双眼明亮逼人,直言拆穿他的诡计,说他是想把自己拖进泥潭,好掩盖自身的龌龊。
柳守义被说得浑身发抖,像被扒光了衣服,一句话也说不出,灰溜溜地逃回了家。
又过了几日,苏珩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清溪镇。净心斋门窗擦得干净,桌椅摆得整齐,只剩周御史用过的冰裂纹茶杯,碎在案上。
柳守义的茶摊生意愈发红火,可他却落下个毛病。每晚打烊后,必用清水擦桌十几遍,磨平木纹仍觉不干净。
有月亮的夜晚,他总恍惚看见苏珩在老槐树下浇水,那身影成了他挥之不去的心病,旁人一提干净二字,他就浑身不自在。
次年春天,老槐树下埋鱼肠的地方,竟冒出了新枝。夏日一到,开满了满树白花,香气清冽透心,镇里人都称奇。
有人给这树起了名,叫“浊地清槐”。柳守义摘了几朵槐花泡茶,粗瓷碗里的茶汤,竟带着清苦回甘。
他喝着茶,眼泪忽然掉了下来。这时才明白,苏珩擦的从不是桌椅,而是本心;他毁掉的,也是自己对洁净的敬畏。
运河水依旧浑浊178炒股配资论坛网,柳守义坐在茶摊前发呆。茶碗依旧油腻,可他心里却空了一块,这辈子都填不满了。
发布于:吉林省富牛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